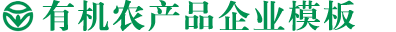新闻资讯
咨询热线
0898-08980898传真:0898-08980898
【神农架第二届网评征集145】散文:神农架酒脉里的自然与文明
北纬30度的清晨,雾还在山腰缠着。一滴水从石缝落下,砸进潭底,声音很小,但听得见。只有山自己,在慢慢醒。酒脉就藏在这里,不响,不闹,不在热搜上,但它一直都在神农架。
“神农尝百草,识五谷,取山泉作醴,以疗民疾。”这个“醴”不是烈酒,是甜醪,喝起来微醺,暖胃。古时候,拿来治病。酒,最早是药。
这片土地上的人,早就懂“变”,把粮食变成了美酒,不变的是初心,代代传承。
现在,红坪镇还有人这么干。老田,七十五岁,土家族,背有点驼,手很稳。每年秋收后,他带孙子上山,采草药,带露水的那种,七种,不全认得名字,本地话叫“酒娘草”。混上糯高粱,拌匀,封进陶坛,埋起来。不告诉别人位置。“怕人挖走”,他笑着说:“也怕惊了它。”
他们不说“酿酒”,说“养酒”。听坛子有没有“咕嘟”声,看封泥裂不裂,像看一个睡着的孩子。开坛那天,全家围坐,插竹管,吸着喝。第一口,洒地上。“敬山。”“敬树。”“敬老祖宗。”没人说话。风过林梢,酒气浮在空气里,淡淡的,像草木呼吸。这不是表演,是活着的习惯。酒从山来,喝一口,得还一口。
劲牌神农架酒业的车间很安静,不像工厂,像实验室。墙上挂着电子屏,数字跳动:水源地,神农谷,pH 7.2,锶含量 0.31 mg/L。数据每小时更新一次。王工是质检员,穿白大褂,说话慢。“我们取水,穿了十层岩,过滤了十几年。我们不敢乱动它。”他拧开一瓶,递过来。水清得很,喝一口,舌根有点甜。
他们建了生态带,十公里,不让车进。取样要穿无菌服。“不是作秀。”他说,“是怕脏了源头。”实验室里,玻璃皿排成行,泥土样本来自海拔2000米的冷杉林下。科研员小林指着显微镜:“这菌,只在这片林子有。低温发酵,慢,但香,是松针味。”
他们不急。传统“九蒸九酿”,一遍一遍蒸,一遍一遍发酵。现在加了温控系统,误差控制在±0.5℃,精准。但张师傅站在池边,还是习惯弯腰用手曲料里。手指没入三寸深,指尖先触到表层的温热,再往下探,能摸到一丝丝凉润。“机器知道温度。”他搓着指尖,“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手感。干了,湿了,热了,闷了——手知道。”
他把手凑近鼻尖闻了闻,又捻了捻,“你看这曲料,攥紧了能成团,松开轻轻一颠就散,这才是‘醒’透了。” 阳光从车间天窗斜照进来,落在他沾着曲粉的手背上,纹路里都泛着米白色的光。
“机器算得准,但这手里的劲儿、眼里的色、鼻里的味,是老祖宗传的‘谱’,机器学不来。”他笑了:“以前看天,现在,懂天。”科技没取代经验,它只是让经验,少走点弯路。
酒,开始走出山。包装换了,不用塑料,用可降解材料。有的礼盒试了冷杉树皮纤维压的板,还在测,容易裂,但方向是对的——少留点东西在山里。
大九湖边上开了个小馆,叫“酒语”,不大,木头房子,屋顶长着苔。游客可以踩曲,用脚,像老法子。田茂堂的孙子在教:“用力要匀,不能急。”孩子们踩完,笑得直喘。角落里,有人戴AR眼镜,画面里一个穿麻衣的人蹲在溪边,把草药放进陶瓮。没人解说,就看,看久了,心会静。
小陈是本地人,以前在武汉唱歌吧驻唱,去年回来了。“外面唱得再好,听的人看不见山。”她弹吉他,唱自己写的:“山风不说话,只把酒香捎回家。谁在月下等,一坛香天下……”她说,现在有人来,不只为金丝猴,也问:“这酒,真是山里酿的?”“水,真是从石头缝里来的?”“你们,真把钱拿去种树?”她回答:“我们做了,不一定都成,但实践是检验的标准。”
林区文旅局的年报写了,去年,为“文化体验”而来的游客更多了……民宿火了,村里的高粱,不够用了。企业坚持部分收益投回生态保护,但村里人知道,去年修了护坡路,清了溪沟,生活越来越好了。
傍晚,张师傅提着酒坛,往屋后走。溪水浅,石子白。他舀出一勺新酒,轻轻倒进水里。酒液散开,像雾,香味浮起来,又被风带走。“规矩。”他说,“还一点给山。”水继续流,带着那点酒,往下游去。
六千年前,也许也有人这么做过,在某个陶甗边,轻轻倒下第一口。那时没有数据,没有品牌,只有手,有心,有山。现在我们有了更多工具,更多声音,更多路。但最根本的事没变:你怎么对待山,山就怎么回你。
神农架的酒脉,是山写给时光的情书。酒,不是谁酿的,是山,一点一点,酿出来的。我们喝下的,是水,是草,是时间,是自然的精华,是人和山之间那些久远的默契。